研究所簡介
浙江(義烏)商成市場研究所是義烏市商興成市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設的研究機構。研究所以“興旺專業市場,成就商業地產”為宗旨,專業致力于商品交易市場、專業批發市場的研究。擁有一批精通國內外市場狀況、經驗豐富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還邀請了商業地產界及學界知名的專家作為特約研究員或顧問。研究所發展目標是打造民營經濟研究院行業研究所品牌,并成為國內商業地產研究……
業務范圍
聯系方式
中國制造標本:最大領帶生產基地無任何話語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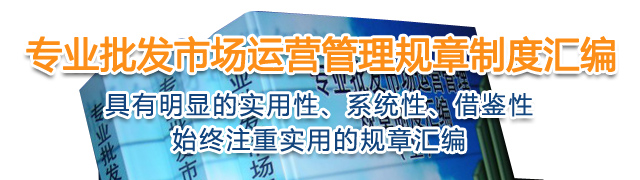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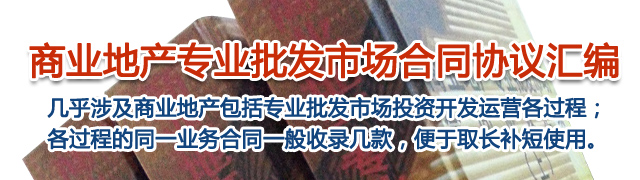 |
嵊州領帶:失語的“世界之最”
戴著“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卻說了不算、沒有任何話語權
浙江省嵊州市是世界最大的領帶生產基地之一,這個“領帶之都”曾自豪地聲稱“給地球系上了領帶”。
然而,這個“世界之最”近幾年卻面臨著從上游到下游都被別人掌控在手中、產品附加值低的苦惱。而隨著今年以來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不斷暴漲,企業利潤嚴重萎縮,幾乎難以支撐。
觀察和解剖嵊州領帶所面臨的產業困境,其實具有標本意義,它的某些產業局限正是浙江制造甚至中國制造的通病。
誰在卡“世界之最”的脖子
到底是制造業大省還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惱存在于浙江多個行業。
嵊州隸屬浙江省的紹興市。曾依托化纖起家的紹興,用一根根滌綸絲編制了一個龐大的產業群。領帶、襪子等產業,就是紹興紡織業中的最典型代表。
嵊州市的領帶產業自1984年起步以來,目前擁有領帶企業千余家,年產值超過百億元,成為嵊州經濟的支柱產業。“嵊州年產領帶3.5億條,從量的角度上看位居全球第一,占全國的90%,世界的40%。”嵊州市領帶行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周慶余說。不少嵊州人曾自豪地說,他們“給地球系上了領帶”。
令人尷尬的是,嵊州市的領帶產業雖戴著“世界之最”的大帽子,卻是一個說了不算、沒有任何話語權的“世界之最”。業內人士注意到,主要原因是其在上游的原材料供應鏈與下游的價格鏈都缺乏話語權,命運總掌控在別人手里。
上游原材料成本的波動始終卡著嵊州領帶的脖子。領帶真絲用量巨大,嵊州市每年真絲用量達7000噸,其中95%需要在外地采購。由于原材料對外依存度大,價格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給領帶企業帶來陣陣“寒意”。今年春繭收購價同比增長60%,前七個月絲價增長40%,從去年的每噸24萬元到今年7月份突破30萬元。
周慶余算過,絲價每噸上漲1萬元,每米面料增加4元成本,每條領帶成本增加0.4元。“按目前的絲價,我們已沒有利潤可言。”周慶余說,“企業已經堅持半年多了,絲價如果不降,恐怕撐不下去了。”
在上游成本擠壓的同時,下游銷售缺乏價格話語權。大量訂單掌握在中間商手中,高額利潤被截留。嵊州市最大的領帶生產企業之一、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說,以一條嵊州領帶在國際市場上銷售30美元測算,國外終端品牌企業在商店中銷售賺取15美元,拿到品牌經營權的中間商賺取12美元,只給本地生產企業留下3美元的出廠價。
“這些中間商牢牢把控流通渠道,不會讓出。”金耀說,“我們曾計劃收購一家英國從事中間商業務的公司,馬上受到國外批發商‘轉移訂單、停掉業務’的威脅,各種制裁迅速跟上來,收購不得不放棄。除非我們放棄加工,專門做中間商,可這要顛覆整個產業的定位。”
產品低端,沒有話語權,這正是量大利低的“中國制造”的特點。在紹興其它地方,在浙江省,不少以加工出身的行業對品牌幾乎是忽略的,有的縣市支柱產業中,甚至一半以上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品牌,只能替人做嫁衣。
到底是制造業大省還是“打工大省”?“世界之最”的苦惱同樣存在于其它行業。浙江會制造服裝,有的服裝卻不如其他品牌服裝的紐扣值錢;浙江會制造眼鏡,可有的產品不如別的企業一個眼鏡盒值錢;浙江會制造布匹,可100米布不如別人的一條手帕值錢;浙江會制造打火機,可有的打火機不如別人的火柴值錢。
面對上擠下壓的“卡脖子”處境,嵊州領帶不得不通過考慮提價的問題。自2008年以來,嵊州領帶行業協會先后兩次提價:一次是在2008年每條領帶最終漲價0.1美元;一次是今年5月,每條再漲0.1到0.25美元不等。“這兩次提價難度極大,需要對內終止價格戰、統一企業認識,對外同國際采購商展開馬拉松式談判,而且最后也只是保本微利。漲價10美分都這么費勁,看來再想吃這碗飯就必須得換換腦筋了!”
“量到天花板了,利潤卻還在地板上”
嵊州市委書記郭敏說:“即使全世界的領帶都歸嵊州生產,也難以支撐起整個市域經濟的發展。”
“量都做到天花板了,可利潤十分稀薄,還在地板上。”在嵊州市,這是從政府到企業談起領帶產業時常說的一句話。在當地不少領帶企業心目中,量大利薄成為一大痛處。
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目前嵊州領帶還只是賺取中間環節的利潤,非常稀薄,在從生產到終端產品整個利潤鏈條上,只占10%的比重,還有90%的提升空間,產值提升空間更是巨大。與其說嵊州是領帶制造大市,還不如說是打工大市。嵊州市委書記郭敏說,“嵊州領帶雖然在量上已達到產業的天花板,可質的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
有的嵊州領帶企業主說,量不大,利潤卻很高,在世界上就有范例。同嵊州一樣,意大利的科墨市也是該國的領帶之鄉,但是領帶的產值充其量也不過是全部工業產值的1/5。科墨用于制造領帶的手工繪制絲綢面料,每種款式只印100米,但每米價格卻以百歐元計。近五年間,科墨市雖然還是領帶主產地,可大部分加工環節已轉移到嵊州,而提供設計、持有品牌的科墨市領帶卻拿走了大部分利潤。在國際市場上,科墨的領帶一條可以賣到上百美元,嵊州的領帶最多只能賣幾十美元,而且即使在這幾十美元的價格中,嵊州領帶企業賺取的加工費也只有幾美元。
正如長三角地區許多地方的制造業中心一樣,在過去20多年間,嵊州領帶的起家、勃興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史。領帶作為一種輕紡工業,由于其門檻低,一時間,缺乏資金、技術的大量農民涌入這一產業。嵊州領帶正是依靠“大批量、低價位”的優勢,在世界產業分工中,將緣起于西方國家的領帶產業轉移到東方,深圳、香港、臺灣、韓國、日本、意大利等地領帶產業大規模向嵊州轉移,如韓國在嵊州投資的領帶企業就達到30家。
可時至今日,日趨稀薄的利潤已成為制約產業甚至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以量為榮的發展方式遇到了巨大的挑戰。郭敏說:“即使全世界的領帶都歸嵊州生產,也難以支撐起整個市域經濟的發展。”
打造一條“垂直產業鏈”
事實上,以加工環節為主的浙江制造業,在歷經20多年的發展中多數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目前,嵊州市從政府到企業在生產環節上正全力向上游與下游拉伸,力爭改變以加工為主業的發展方式,把巨大的成本壓力向兩端釋放,把微薄的利潤空間向兩端拓展。
在上游,嵊州市鼓勵企業外拓原料生產基地。一個多月前,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就遠赴四川省,與當地政府洽談設立蠶桑生產基地事宜。為提高原材料的自主掌控能力,12家領帶生產企業分成兩批,同云南、四川、廣西等地實施“東桑西移”工程的縣市達成多項協議,累計建立蠶桑繭絲生產基地約百萬畝,有的企業還通過控股當地絲綢公司的方式,確保原材料的穩定供應。
據嵊州市政府預計,這些項目全部投產后每年可以產絲近8000噸,不僅能保證嵊州領帶企業的用絲需要,還可以面向國內其他用絲單位銷售白廠絲4000噸左右。為此,市政府每年出資200萬元,設立外拓蠶桑基地專項基金。在浙江嘉興市,嵊州市的領帶企業也把目光放在了當地的供絲大戶身上,把對方納入自己的采購體系當中。
目前,嵊州市還正籌劃建立繭絲調配中心,但這項工作難度更大,需要國家有關部門支持。周慶余說,如果組建一個可儲備3000噸到5000噸的蠶桑繭絲儲備倉庫,可能比建立蠶桑基地速度更快捷、更有效。然而,這樣一個倉庫需要投資10億元到15億元,對地方財政與正處于微利的行業來說壓力太大,如果沒有國家有關部門的協調與銀行的支持,難度可想而知。
在下游,嵊州市加強品牌運作,進軍終端銷售市場。嵊州市經貿局副局長邢昌陸說,政府拿出專門資金鼓勵自主品牌出口、鼓勵收購國外品牌、鼓勵國外注冊商標等。浙江丹魯依服飾有限公司利用歐洲經濟波動的時機,同國外品牌公司合作,在東歐創辦一家終端銷售業務公司。董事長袁小平說:“我們出資,對方以品牌入股,合作協議約定,我們可以分享對方品牌帶來的終端銷售利潤。”此外,巴貝公司收購了意大利一家以設計領帶著稱的公司,宏達制衣公司把設計工作室辦到米蘭,并引進臺灣針織大師潘怡良為旗下品牌的設計總監。
一位研究人員形象地說,嵊州領帶產業眼下最需要上下伸個懶腰,把自己的空間騰得更大一些。事實上,以加工環節為主的浙江制造業,在歷經20多年的發展中多數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現在的浙江省,包括領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并力爭打造一條從上到下、縱向一體的“垂直產業鏈”,從而使企業便于從各個環節對產品成本、質量及生產節奏進行控制。
行業“世界之最”、“單打冠軍”的嵊州領帶,正在用自己擺脫陣痛陰影的實踐,為其它戴著光環的“中國制造”敲響警鐘。
嵊州領帶的新“算式”:
企業做“減法”產業變“乘法”
記者李亞彪商意盈杭州報道
同浙江省許多地方塊狀經濟的“發家史”一樣,作為輕紡工業的領帶,由于其門檻低,當年大量農民涌入這一產業。“稍微有點規模的領帶企業幾乎什么都做。”一位業內人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從原料采購、到印染、再到打線,企業幾乎每個環節都親力親為,是真真正正的‘小而全’”。
這一嵊州領帶早年的真實寫照,在近兩年間開始發生悄然變化:部分領帶企業開始做起“減法”,退出部分生產環節,重新細化分工,整合產業鏈,卻實現了整體產業變“乘法”的效果。
產業鏈整合產生“化學反應”
“擴大再生產不僅僅依靠投資,而是要通過合作,這不僅僅是物理反應,更是化學反應。如果我們不通過合作的方式去提升話語權,就是死路一條。”袁小平說。
過去,嵊州領帶企業由于“小而全”,沒法做到“大而專”,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浙江丹魯依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袁小平說,嵊州過去再小的領帶生產企業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都建有自己的倉庫,養著幾部運輸車輛,自購原材料、自辦運輸,庫存壓力大,生產成本高。他算了筆賬:減少一個鍋爐可節約幾十萬元,如果在研發、物流和倉儲等方面進行整合,七八家大企業的整個資金用量至少可以減少1億元,成本減少8%到10%。
巴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金耀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一般從生產企業來講,生產這一環節的價格要提升非常難。因為內部已經經過了充分競爭,利潤趨于平均,會穩定在一個正常的產業利潤率,沒法達到高額利潤。“要增加毛利空間,必須轉變發展模式,整合產業鏈。即使量減少,利潤可能是更高,價值會極大地提升。”金耀說。
華業絲綢等3家面料后整理企業原本是競爭對手,常常會在同一家領帶企業“狹路相逢”,內部競爭嚴重削弱了競爭力。經重組后成立了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退出生產和流通環節,實行技術、人才、市場共享,并分擔市場收益和風險。昔日的行業“對頭”經過整合,成為了嵊州市最大的領帶后整理企業,掌握了嵊州90%領帶后整理外加工業務。與此同時,一大批領帶生產企業則把后整理業務從企業剝離。
“產業鏈整合后,可以讓小企業退出某些生產環節,專心于生產或加工,減少不必要的資金投入,并擺脫同質化競爭的困境,形成差異化發展。同時,各個企業間嵌合更緊密了,相比于同樣具有廉價加工優勢的越南和印度,整體優勢也更加明顯了,產業穩定性也提高了,不會輕易轉移。從這個方面來講,傳統產業的生命周期也將被延長。”經歷了大整合后的金耀信心十足地說。
大企業構筑“大平臺”
由于產業集群中涌現出龍頭企業,出現越來越多龍頭企業也參與到為整個產業鏈提供平臺服務的新趨勢。
同產業鏈整合相伴生的是,一批大型龍頭企業在嵊州市領帶塊狀經濟區中崛起,他們與政府一起,為區域內所有的中小企業構筑了發展的空間平臺、公共服務平臺,托起了整個產業鏈。
嵊州領帶塊狀經濟區過去以中小企業為主,近兩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龍頭企業,自2007年起,巴貝、好運來、麥地郎等多家龍頭企業的銷售額就達到1億元以上。這些龍頭企業將“外拓基地、原材料采購、印染、打線”等程序整合到一起,實現生產統一管理;原材料對外統一采購;色絲對內統一配送。僅統一“團購”這個環節,每噸白廠絲的采購成本,至少可以節約500元。其中巴貝集團還投資了600萬元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領帶花型電子資料庫,目前已入庫30萬個花型,嵊州麥地郎服飾有限公司投資2500萬元的數碼面料花型設計研發中心也已經啟動,而這些大平臺的資源都可以供本地企業共享。
地方政府也牽頭創立公共服務平臺,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大發展空間。嵊州市正計劃新建一個中國嵊州領帶城物流中心,形成集交易、展示、技術、科研、倉儲、加工、休閑觀光、信息發布、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功能于一體的現代化專業市場群。
嵊州市領帶協會常務副秘書長周慶余說,過去構建企業公共服務的大平臺都是政府“唱主角”,現在由于產業集群中涌現出龍頭企業,出現越來越多龍頭企業也參與到為整個產業鏈提供平臺服務的新趨勢。
從“領帶之都”邁向“真絲之都”
袁小平說,他們正新建一萬多平方米的廠房,用于向真絲為主的服裝產業拓展。“這種拓展不是盲目擴張,我們沒有離自己的主業太遠,而且也不會放棄主業。”
嵊州領帶產業為尋找新的增長點,積極橫向朝相關產業拓展,謀求從“領帶之都”向“真絲之都”的轉變。
從領帶產業往真絲產業轉移,嵊州有天然的優勢。周慶余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全球家紡正處于上升期,真絲家紡與領帶一樣都是提花產品,兩者技術、設備、設計相通,客戶重合度也高,領帶產業做家紡風險相對較小。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最先進的電腦提花織機60%以上在嵊州。嵊州市市長盛秋平說,全市真絲用量已達7000噸左右,占全國真絲用量的10%,出口產品占全國的六分之一。不少領帶企業除了領帶以外,真絲產品越來越多。原來從領帶產業起步的巴貝集團,去年男裝、家紡產值已占全部產值的38%。有的領帶生產企業的針織服裝占全部產值的比重甚至超過一半。
據了解,嵊州市從去年開始提出一項“真絲拓展計劃”,力爭通過五年左右努力,投入50億元,真絲用量占全國的20%左右,在鞏固原先領帶和針織產業的基礎上,努力打造全球真絲產品集聚地。
在領帶生產企業丹魯依服飾有限公司大院,《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一大片廠房正在緊張建設中。公司董事長袁小平說,他們正新建一萬多平方米的廠房,用于向真絲為主的服裝產業拓展。“這種拓展不是盲目擴張,我們沒有離自己的主業太遠,而且也不會放棄主業。”他說,“轉變發展方式跨度太大,是很不冷靜的行為。”
巴貝公司的真絲產品已經從領帶延伸到高檔的相關面料上,包括窗簾、床上用品,箱包面料、男裝、室內軟裝修等多個方面。“這樣的延伸對我們公司來講發展空間很大,而在真絲家紡面料方面,我們的技術和經驗優勢非常明顯。”金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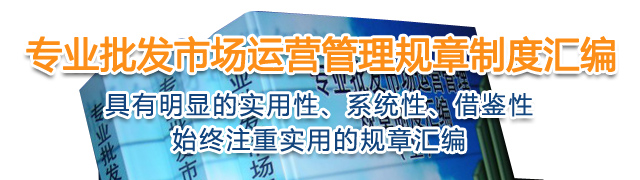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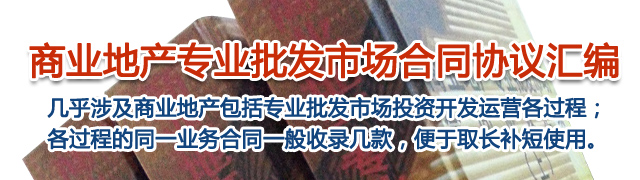 |
點擊次數:707

